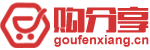老广东年菜预热中
如果说有四个字可以解决中国人在农历腊月二十八之后到正月十五之前的所有纷争,那就是“大过年的”。它和“来都来了”、“给个面子”、“还是孩子”并列为中国四大和谐妙语。而相比其它三个,“大过年的”适用期非常短,但效力却相当大。就算当事人双方有天大的矛盾,一听到这句话,百分之八九十都会如醍醐灌顶一般顿悟,对啊,大过年的,我跟你争个什么劲儿啊?
之所以一说过年就能风波不起,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个合家团圆,一派祥和的时候,个人要以大局为重,能忍则忍。另一方面,中国人相信,一年之计在于春,春之际又在于春节。若要在这个时节吵架斗狠,那真是跟自己一年运气过不去了。不但不能动气,还要用各种方法来催旺这运气。比如吃,就要吃吉祥的东西,意头菜就是这么来的。所谓意头菜,就是利用谐音、意会等方法,让菜肴至少从名字来看,真是吉祥又如意,团圆又美满。
关于“好事大利”的遐想
若说广州的意头菜里,新春必备就是“好事大利”。这道脍炙人口的佳肴,春节期间酒楼食肆必入菜谱,不少家庭也有烹制此菜的风俗习惯。“好事大利”这个名字主要来自于两样食材,蚝豉和猪舌,“蚝豉”自然是“好事”的谐音。“舌”在广东话里叫“脷”,自然就成了“大利”。这道菜并不难做,烧锅下油,爆香姜片、葱段、蒜头,加入上汤、绍酒、蚝豉、冬菇、各种调料,慢火将蚝豉煮至软。将焯熟的生菜围边,蚝豉、冬菇上碟,卤熟的猪舌切片上碟,原汁勾薄芡淋上便成。
要说多好吃,这道还真不算,但谁让人家意头好呢?可如意头菜的创始人脑洞开大那么一点,多想了那么一点,口齿不清了那么一点,意头菜的意头可能就变了。在普通话里关于舌的词可大多不是很好,比如“多嘴多舌”、“油嘴滑舌”、“口舌之争”、“鹦鹉学舌”等等。就算是“利”,怎么就能保证是大利?也有可能追了半天却是“蝇头小利”,没准还是“自私自利”、“急功近利”呢。还有那个蚝豉,谐音到“好事”。好字却是多音字,如果是四声,好变成动词,就成了“好事之徒”的“好事”,小小贬义还是有的。
只要意头好,炸炸也无妨
广州人终年不喜油炸食物,所虑者无他,不过“热气”二字。所谓“热气”,就是上火,有些老广州人甚至觉得咖啡和咖喱都热气,更何况油锅里炸的东西乎。但一到过年,这些也就顺带不讲究了。年味是从炸油角、炸煎堆开始的。油角因为形状像“荷包”,一炸就膨胀,取其钱包饱胀的好兆头。煎堆麻团、珍袋,是拳头大小的油炸糯粉团。从“冷手执个热煎堆”这句表示超级好运的俗语里就能听出广东人对它的爱了。
不单是在这些小零嘴上要重油重糖,烈火烹油,贺年菜也喜欢用油炸的方式来进行。过年吃鱼和虾,分别寓意“年年有余”和“笑哈哈”,广州人平时最爱吃的是白灼虾和清蒸鱼,这个时候可能就觉得太素净了。“年年有余”的任务一般会由煎酿鲮鱼来完成。鲮鱼是广东特有的一种淡水鱼,其肉质鲜美,但刺较多,主妇们会将鱼肉与骨刺剥离后,再加入极细碎的马蹄和冬菇及一点陈皮,与精淀粉一起搅拌,然后重新装入鱼皮内,其外形与真鱼完全一样,放入油锅内炸至九成熟,再以各种调料调成汁炖至全熟,最后勾芡淋在鱼上而成。虾就简单多了,挂糊、快炸,做成干炸虾球。能烧得起油锅的人家,想必是过得不错吧。
油炸是最喧哗的烹饪方式,也最浮夸和外露。谁家一烧油锅做炸物,街坊邻里就都能知道。在饥馑年代,这也是一种无声的炫耀。而在当今,人人都买成品的时候,这也成了一种闲情的昭示,或者家庭和美,人丁兴旺的暗喻。既然如此,加之冬天想上火也不那么容易,于是解开一年的油炸之禁,也理所应当了。
健康+美味,是更高端的追求
都说现在有钱人吃健康,没钱人吃调料。能吃得健康,还美味,还有创意,还有意头,绝对是贺年菜更高的追求。每年被邀约吃新春盆菜都因为看不到一点绿色而发愁,这么一大桌高脂肪、高蛋白和高糖大菜里过一个年,还真是辛苦。
曾经吃过一道贺年菜叫“福如东海”也貌似合理:下面一层如波浪般的伊面,再铺一层海参,然后是错落铺排的小胡萝卜和生菜。生菜是“生财”,小胡萝卜寓意“鸿运当头”。食材考究,营养搭配合理,还不落俗套。还见过以淮山、杞子等药材做汤底,以花雕和白兰地做佐酒的火馅醉虾,热锅沸着吃,暖香满室,吃完醉虾再喝汤,名叫“生龙活虎”。
如果自己在家做,也可来个甜品“四宝汤圆”。买湾仔码头的水晶彩色汤圆就行。外面一层水晶皮,里面黄色丸子是南瓜,紫色丸子是紫薯,还有黑芝麻的、核桃的,若用杏仁做汤,全部的色彩都来自食材的天然本色;年宴也应该要让人吃出幸福甜美,配杏汁做汤不但美,还取了谐音的“幸”的美意。美食、美貌、美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