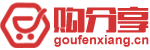翻毛月饼和瓜仁油松饼结成的姻缘
2015年08月28日 中国烹饪杂志 文/王希富 插画/郑莉

故事要从我的外祖父和祖父初识时说起。晚清时期的光绪年间,我的外祖父陈光寿在内务府所属的御茶膳房任小职,家住烟袋斜街。清早,他揣着腰牌,徒步走向紫禁城后门,路过天汇轩茶馆,便进去喝茶吃点心,遇到熟人、朋友,打招呼聊上几句。可巧,那时祖父王文山家住黄化门,每天也是揣着腰牌进宫,为皇上和宫妃赶骡车,于是一清早也先到天汇轩喝茶,吃点心。本来都是在宫里当差,又都属内务府管辖,这两位便抬头不见低头见,开始彼此挺客气,见面点点头,各吃各的点心。后来,彼此总要让座,让茶点。再后来,便是谁先到谁叫茶点、谁结账。老哥俩相差十几岁,一位祖籍山东,闯关东又进京到了御膳房当差,家世为老勤行;一位祖籍北京张家湾,是脚行。
早年间,京城十三仓的粮食均从南方沿运河漕运到京,张家湾便是一个重要的码头。到清晚时期,漕运已经不能到达京城,便从张家湾开出骡车队,向京城运粮,因此,张家湾也是脚行发达之地,祖父王文山一辈就进宫赶骡车了。
话说回来,后来陈、王两位老人不但是宫里当差的朋友,也是天汇轩喝茶的茶友。两人虽然经常在宫里宫外见面,但是彼此都没进过对方的家门,也没有其他方面的深交。
这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京城秋高气爽,难得两位有兴致,清早便来到天汇轩茶馆。掌柜的和跑堂的都与二位熟悉,便张罗里屋一个单间落座。茶馆的单间一般不同于庄馆的雅座,只和外屋有一隔扇,隔扇门帘却总是高挑,一是为了随时照顾顾客添茶倒水,二是便于掌柜的“瞭高”,避免人多手杂时出事端。
二人一落座,彼此相视而笑。笑从何来?因为当天是八月十五。两人各提着一包饽饽,放在桌上。外祖父年纪长祖父十几岁,故此祖父便先问道:“大哥,今天八月十五,难道咱家还用给嫂子买饽饽过节吗?”外祖父哈哈一笑,说:“这话倒该我来问你呀,你提着这包饽饽是给弟妹呀,还是送礼呀?”祖父说:“不瞒您说,我家大小子自从离开会贤堂,就到了致美楼,由于遇到一位姑苏的师傅,想着姑苏点心细腻、讲究,便学了白案。自己总说致美楼饽饽如何了得,我却不信,怕这孩子自鸣得意,今天又是八月节,故此,拿来一包他们所制作的翻毛月饼,请大哥指教。”说完,打开点心包,露出整整齐齐八块月饼。外祖父陈光寿扫了一眼,见这月饼半斤一块,洁白如雪,温润如酥。虽说是酥皮,可包里包外没落一片残渣碎片,恰似和田白玉琢磨而成。心中暗暗赞叹:“这孩子果然身手不凡,的确是经过名师指教,也加上自己的苦心磨练。”此时,早有伙计拿来碟筷,装盘一块,切开再看,那心馅果料新鲜、均匀,糖面搓得散落酥松,红绿白黄,色泽喜人。伙计改刀,外祖父陈光寿拿起一块放入口中,闭目细品,半天无语。祖父待了一会儿,便问道:“大哥,您以为这月饼做得如何?”外祖父说:“这样的月饼可以和御茶膳房相比,可惜,殿臣不是我家陈明,如若他两个调换,他将来就会接续我的官差进宫了。”
外祖父口中的“殿臣”,就是家父,当然那时他还是尚未成亲的小伙。祖父见外祖父夸奖自己的长子,便道:“您这话实在是夸他了,可他哪里有如此的福分,将来还是陈明接续您的。”外祖父听了,叹气道:“陈明无心再做勤行,总想舞枪弄棒。还真怕将来会惹下什么祸端。”祖父听了忙道:“大哥,陈明的聪慧我家殿臣无法可比,京城谁不知他那名堂的手艺和模样。那是要做大事情的。”

尝过了父亲的翻毛月饼,又尝外祖父的点心瓜仁油松饼,外祖父说:“其实,翻毛月饼也是宫廷饽饽,只是不是平日御膳中的常品。因为御膳所供的饽饽,无论何种,都必须按照内务府要求制作,特别是分量大小都非常严格。”这与皇上用膳的规矩有关。皇上用膳时饽饽是直接入口,一般不切不掰,尽量减少他人对御膳的接触;另外也避免饽饽掉落残渣,挂于口、脸或龙袍之上。所以,御膳饽饽要求最大不超过一两,这样也显得精致、细腻。而翻毛月饼是作为寿宴时供奉之“饽饽桌子”的,而且是作为底托位置,故此个头必须够大,不然,饽饽无法码成几尺之高。
瓜仁油松饼则比翻毛月饼小而细腻,外祖父说,这是内务府每年中秋时节制作的一种月饼,算是宫廷细点,由内务府下到所属各大部门,全是皇上的恩典。从大学士、军机大臣,到六部、九卿、都察院、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顺天府衙门、兵马司指挥,都能得到这种恩典月饼。祖父说:“瓜仁油松饼早有名气,据说制作精细,还有秘方。”外祖父说:“哪里有什么秘方,只是比那普通饽饽更为费手,尤其是‘油松’,不是使用普通松仁那么简单,而是必须要用东北贡品松子,一半破粒入馅,一半榨油拌馅,所以饽饽馅松子香气浓厚清雅,可以补气安神。一般饽饽铺绝不会花费此功。”说罢,切开,让祖父品尝。祖父尝罢一口,连连叫绝,说:“真是香气能入肺腑,柔软细腻如泥。”外祖父说:“今天拿来,是我在家亲手所做,请你和弟妹尝尝,以后也让殿臣学一学宫廷的饽饽手艺。”祖父说:“陈明的精明,殿臣是绝不可比,可是,殿臣这孩子老成持重,办事极是认真,要学宫廷手艺,就必须拜师您的门下,不知您的意下如何?”外祖父当时哈哈一笑,就答应了收徒之事。
从此,父亲就算又拜了一位宫廷茶御膳房的师父,除了南味茶食糕点,还开始学做宫廷细点和满式饽饽,如萨其马、芙蓉糕、奶乌他、奶卷子、孙尼额芬白糕等。后来,父亲在行里算是制作满汉饽饽的能手。那时,京城不少饽饽铺皆称“南北细点,满汉饽饽”,但传承正宗的手艺确不多见。有一位大收藏家常去致美楼吃饭,与父亲倒也很是熟悉,极爱吃父亲制作的翻毛月饼,曾提笔在父亲的饽饽磕子上写过“人间福寿饼,天下致美楼”的诗句,以为赞叹。
后来,陈、王两家便有了来往,才知道父亲是王家独子,陈家也是独女,也就是笔者的母亲。交往之中,两家日深月久以心印心,便几乎成了一家。那时,父亲十八九岁,正值青春年少,面容稍胖,但五官端正,秉性温和,后来也收了不少徒弟,在勤行便小有名气。母亲是极有教养的,也是大家闺秀,京绣手艺出色,无论是衣褂鞋裙还是被褥床单,飞针走线绣出云龙飞凤、山水花鸟,远近街坊无不夸奖。母亲还会唱曲,那时常唱的《子弟书》、《莲花落》、《牌子曲》、《太平歌词》,展现着从老年间封闭生活到晚清、民国时期的老北京生活变迁。母亲受外祖父的影响,又受到当时社会变迁妇女活动的影响,自幼便有武功的底蕴,不但拳脚了得,还会弓箭飞镖。就这样,父亲和母亲,一文一武,被外祖父和祖父说和到一起,两家便又成了亲家关系。
母亲不是勤行,但是母亲自幼便在家和外祖母学习做饭。外祖母长期在大宅门做饭,传授给母亲的家常闾巷菜品不下百种,加上外祖父的传授,母亲的手艺绝不低于普通二荤铺的头灶师傅。至今,我和我的孩子以及老亲近邻有关系的各辈亲戚,还总是回味母亲的烹饪手艺。

后来,两家定亲,在外馆骆驼桥买了一所小四合院,择吉日办喜事,高搭喜棚,满做彩子花活,所有厨子均是由外祖父派来的徒子徒孙,家伙座一律水磨漆起金线。远亲近邻齐来祝贺,中午是海味席,晚上是烧燎白煮带烧碟。这种两家都是勤行的喜宴在京城并不多见,母亲回忆时,总觉得还是她人生中的一喜。特别是在过门之时,外祖父尤其嘱咐,将“子孙饽饽”由普通的水食(即水饺)改为翻毛月饼和瓜仁油松饼,更代表两家由此而结亲的良缘。而且,翻毛月饼和瓜仁油松饼皆是馅内多子,还象征多子多孙。制作时,又将原有的“福禄寿喜”纹饰改为“荣华富贵”四个字。外祖父还托自己的本家兄弟在景德镇烧了一套当时名噪一时的张子英手绘粉彩富贵白头瓷器,作为母亲的嫁妆,其吉祥内涵就是富贵白头。
后来,我家的四个弟兄便按照“荣华富贵”排列起名。母亲抚养了我们兄弟四人,还有两个姐妹,共是六人,最小的弟弟出生不久即夭折,所以只有我们兄弟姊妹五人,父亲说也算是“五子夺魁”吧。我刚刚懂事时,每天清晨没起床躺在炕上,便总是看着母亲的瓷器,那是硬彩官窑的瓷器,署名张子英作,每件瓷器都有两只栩栩如生的白头鸟和枝叶繁茂、色彩斑斓的牡丹花。张子英用老道浑厚的行楷写着:“独占春台第一筹,文章大块最风流。果能修得汾阳福,富贵绵绵到白头。”岁月的流逝和无端的动乱,把这些象征富贵白头的吉祥瓷器消磨和打落得所剩无几。随着动乱的逝去、改革的春风吹来,我用了十年苦心收集,已经将母亲当年的嫁妆一件不差地收集齐全,用以祭奠勤行先人和继承先人遗留的美好意愿。
后来,翻毛月饼和瓜仁油松饼都与我家发生了密切的关系。父亲的翻毛月饼在京城名噪一时,二哥希华也学了白案手艺,每年八月节前,大哥、二哥都要到致美楼帮父亲做月饼,这两种饽饽也成了我家八月节必要摆盘上供的供品。当然,还有自来白、自来红、提浆月饼等各类应时当令的饽饽,有的供奉,有的不能供奉,便是大家过节的口福了。因为家中我的年纪最小,所以父亲、哥哥都倍加疼爱,一对富贵白头的壮罐里常年都存放着各类饽饽,留给我吃。父亲过世后,家道贫寒,只得降格以求,壮罐内改放火烧。母亲把我带到黑屋内,说所吃就是饽饽,我也是吃惯了嘴的,便一口不吃,说自己是“饽饽嘴,不吃火烧”。此事后来成了家中的笑料。
一包翻毛月饼和一包瓜仁油松饼,让勤行两家结成姻缘,也算是勤行旧事中的一段回忆吧。
购买翻毛月饼的淘宝链接地址
全部评论()